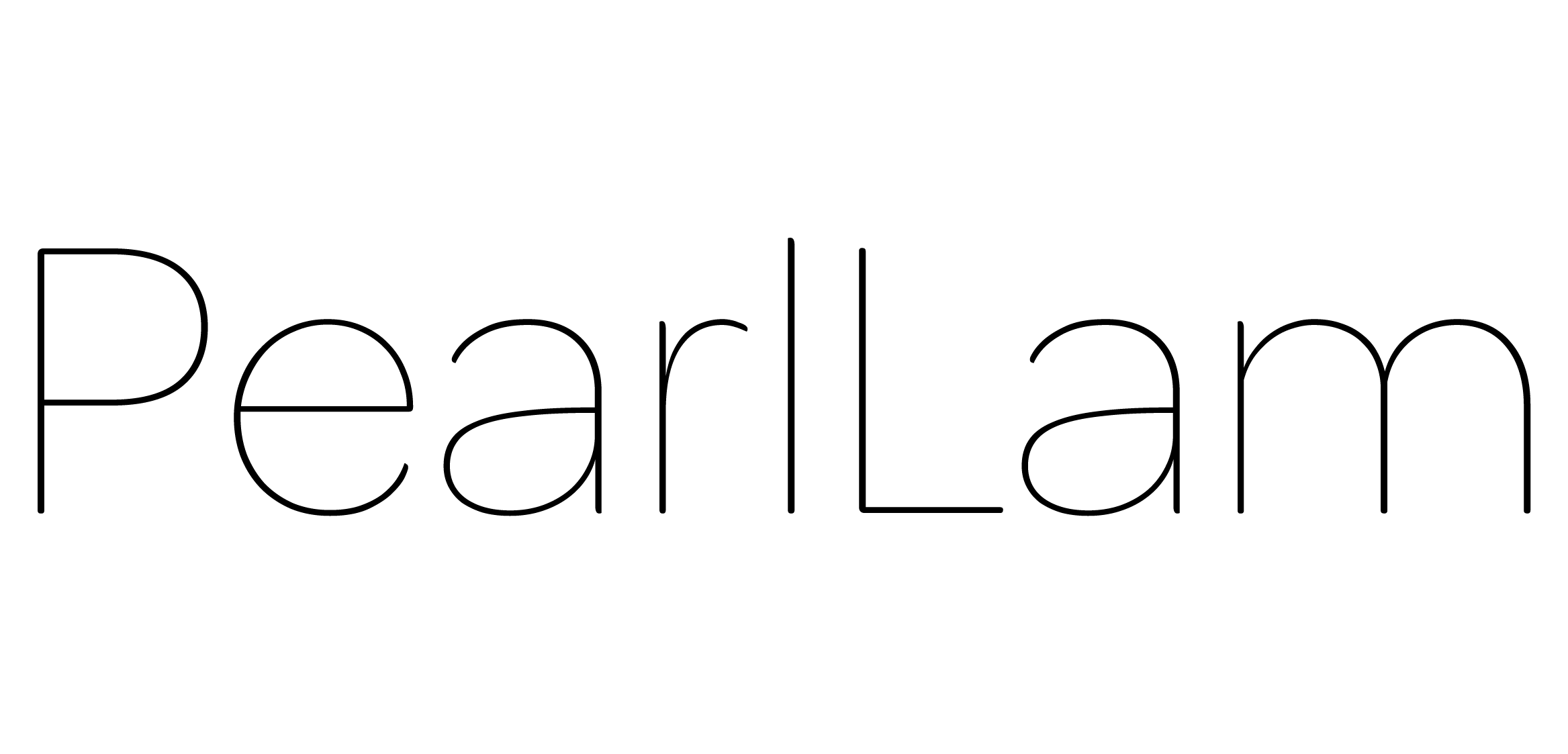陳浩揚是一位與藝術門合作的策展人,他常駐香港和上海,曾擔任奧沙畫廊和上海外灘三號的滬申畫廊擔任總監。
彼得·佩里(Peter Peri), 生於 1971 年, 是一位於英國倫敦工作和生活的英國藝術家。
陳浩揚(陳):您為何將此次展覽取名為《新⽉》?
彼得佩⾥(佩⾥):新⽉通常⽤以描述呈鐮⼑形的⽉相變化,但其原意接近⽣⻓、增⻓、展開。讓我感興趣的是,⼀種精確的⼏何形狀如何使得我們看⻅⼀個不可知的⽆限過程,⽐如成⻓。這樣的關係使我創造了⼀些我想表達的雖可感知但仍充滿神秘的東⻄。
陳:抽象對您來說意味著什麼?
佩⾥:我對抽象的興趣主要在於它的存在是依賴組織,以及這抽像中的機體如何將問題反饋到現實。
陳:您認為抽象與⽣活之間的潛在連結是什麼?
佩⾥:不以世上任何物體去填補空⽩畫布或空⽩紙張,這其中的根本問題在於⼀個⼈必須使⽤某種⾃⾏所創造的體系來促進增⻓。若以思辨體系去填補空⽩則需依賴想像⼒。這個過程解釋了我們作為機體與環境的關係,因為我們⼈類不僅是⼀個複雜的系統,也是⽆數系統,如:⾃然、語⾔、社會,等的⼀部分。
陳:您的作品和您已故祖⽗ Peter László Péri 的構成主義作品有⽆任何形式上的聯繫?
當下的我們可以從構成主義藝術運動中學會什麼?
佩⾥:抽象意味著需要做出切割和減法;我更傾向於認為我的作品是構成主義性質的,⽽不是抽象的,這可能與我透過我祖⽗對構成主義的了解有⼀定程度上的關聯,他是構成主義的先鋒之⼀。我希望我的創作是社會構成性的,因為它著眼於機體和環境之間的系統關係。這其實是俄國⾰命理論家探索的最有趣的途徑之⼀,⽐如對構成主義藝術產⽣了巨⼤影響的亞歷⼭⼤·波格丹諾夫 (Alexander Bogdanov)。
陳:您在此次展覽中有⼀件作品《雙重調節器》,這是引⽤⾃波格丹諾夫的⼀個詞彙。他是 20 紀初影響控制論和系統論的思想家之⼀。您的作品是在評論當今社會及其去物質化現象嗎?
佩⾥:波格丹諾夫關於雙重調節器的想法確實讓我感興趣,因為它描繪了⼀個內部雙重監管體系的形成。雙調節器的概念也成為我此次展覽中的繪畫作品的⼀種呈現模式,⽐如,⼀組特定的顏⾊可以在作品當中相互調節以形成作品的構圖,⼜或者是曲線和直線的交互⽅式。
我認為波格丹諾夫的作品和當今社會還是緊密相關的。就去物質化和互聯⺴⽽⾔,它正是反映出數位資訊的宏觀和集體結構,和我們作為⼈類個體的細微、特例的⾏為之間所發⽣的事件。對我來說,⽆論是在細節上、或極⼩的事物上、還是在保持慎重態度上的強調,都是對這些集體結構⼀種有⼒的反問。
陳:能談談您是如何在繪畫作品中使⽤這樣的模式?
佩⾥:在《諧振的韻律》系列中,我⾸先選擇了⼤概 10 種顏⾊,將它們分為兩組,然後來從每組中再配對不同的顏⾊。每當我的繪畫作品中出現對⾓分界線時,我都會使⽤互補⾊重新開始畫出線條。這些線條在作品中或⽔平地或垂直地相隨,以創造出各種偶然的⾊彩和形式節奏。
在灰⾊作品系列中,如⼈物或瀑布等可辨識的題材,是由我那些快速的筆觸畫出的新⽉和精確地按照它們曲線的邊緣⽽描繪的直線條之間的互動所展⽰。在作品創作的最後階段,有時我會在畫⾯做⼀些調整以加強形象的解讀。
在《雙邏輯》系列中,畫⾯中各個邊⾓由⼀序列的顏⾊隔開,這同⼀序列⼜被放⼤,使得畫⾯背景中勾勒出更多的邊緣。我⾮常重視形式與背景之間的匯合點 — 邊緣、重疊和陰影,都是我所關注的。由此產⽣的畫⾯結構就像是環道或迷宮。
陳:在您的繪畫作品中,⼀切都⾮常精確。您在創作過程中是如何處理畫作⾯中出現的意外或突發狀況?
佩⾥:由於它們是⼿繪的,線條堆疊的⽅式可能會產⽣意想不到的狀況或出現線條在畫⾯中逐漸模糊的情況。這可能是因為我⽤的尺⼦不平整,也可能是畫筆沒了墨⽔,⼜或我⽆意識地過於使勁或鬆懈所導致。這恰好充分說明了這些帶有瑕疵的線條都由我⼿繪。從更⼲的意義上,這些意料之外的狀況也是我在展開不同作品和不同系列之間所形成的敘事⾥必不可少的部分。這其中包含了我身為⼀名藝術家所經歷的失敗、幹擾、僵局、事故和成就。
陳:在您的作品中似乎總有⼀種內在的⽭盾性質,例如,您同時呈現畫⾯的部分和整體、有限和⽆限、諧振和失調。您對此有什麼想法,這些困惑是否最終都得以解決,還是讓觀者繼續陷進困惑?
佩⾥:除了共存,我不認為可能出現,或能有令⼈滿意的解決⽅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