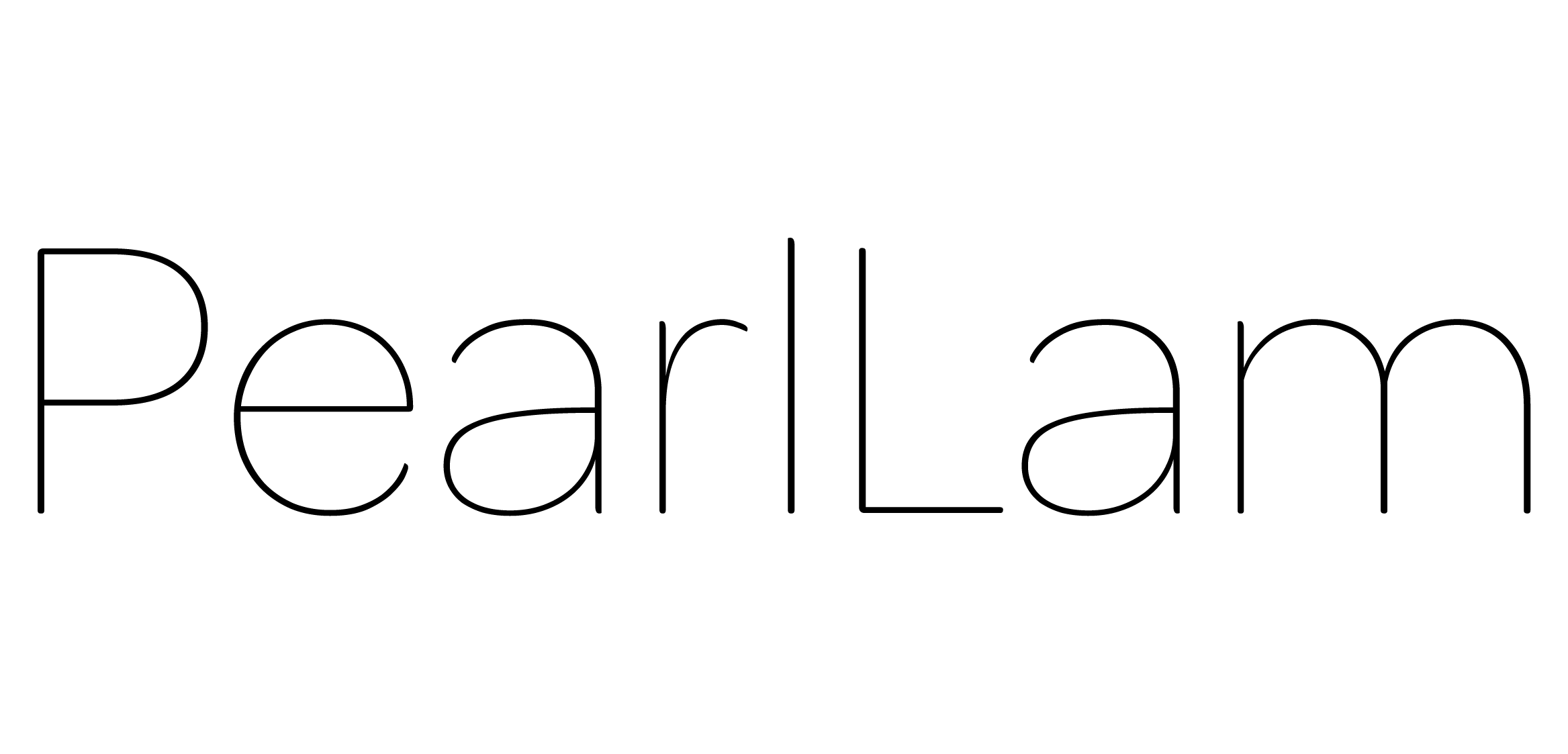概要
出發點與線條的對比:邱振中近期作品
中國人的毛筆製作原理很簡單,即將毫料捆縛於竹制筆管。中國人的墨水同樣取材自最簡單的材料:細煙灰與黏合劑。無論是在原來的形式上,或是採用隨著時間推移而出現的更為精緻、做工複雜的材料,毛筆與墨水能一同創造出許多令人驚歎、創作力豐富、充滿活力的水墨作品。然而,水墨畫在當代社會也面臨了必然的現代性挑戰。許多藝術家,尤其是那些對毛筆的認識不夠精深的,往往未做好準備迎接這一挑戰。相反的,他們在中國視覺文化的發展中創作了“水墨藝術”。水墨藝術並不應與水墨畫所混誵。它們之間的區別經常被認為過於模糊不夠清楚。邱振中經過各種思考以後,在他的藝術理論、他的書法,以及最近的畫作裡,以一種直接的方式響應了這項挑戰。中國古代有天賦的藝術家都會通過文人三絕:詩詞、書法、繪畫以達致修身之道,並創作出具有藝術史意義的作品。但如今我們很難找到能同時很好地體現這三者的藝術家,邱振中可謂是罕見的例子。
邱振中,北京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他在書法、文化研究、語言及詩歌等領域的造詣眾所週知。邱畢業於杭州的中國美術學院(前稱浙江美術學院),碩士學位,邱振中相信書法作品的價值在於其線與空間的表現力而非字元,並致力於將書法創作擴展到當代藝術中。邱於1988年開始創作的《待考文字系列》是其創作進入當代藝術範疇的重要標識。基於來自商周朝代青銅器上無法辨識的文字,此創作系列回歸到中國歷史中。其作品承認人性永恆存在的慾望和相應的交流需求,創作重點落實在線條與空間上。因為這些文字是不可讀的,所以筆觸與空間分割變得尤為重要,同時線條之間的相互作用將筆觸細微之處——包括筆觸的韻律和力度——的表現力揭示無遺。《待考文字系列No. 31》(第x頁)與《待考文字系列No. 32》(第x頁)都是2003年創作的小幅作品,作品將韻律與力度間的對話,疊加在墨色濃淡與筆觸乾湿的變化中。
邱振中指出,傳統的書法是著力展現“文字的藝術”,但是現代的書法則是展現“線條與空間的藝術”。他最近的作品看似完全脫離書法創作,而專注在人物和靜物的創作上,靈感來源似乎相去甚遠:馬蒂斯的畫作和描繪著名中國戲曲《西廂記》的版畫。仔細觀察,則會發現,兩個不同的靈感來源都是與他對中國當代藝術的思考有關,都與他對“線條的藝術”的思考有關。無論是汲取自馬蒂斯的畫作,還是寄託於中國版畫,邱的開放胸襟和系統的構思開創了當代中國水墨的嶄新局面。邱振中認為,中國當代水墨的創作必然與中國傳統和現代西方藝術相關,但是人們對此缺少清晰的認識,常常在背叛與融合之間徘徊不定。邱振中這兩組作品實際上是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當代水墨藝術到底能不能從中國傳統和西方現代藝術中汲取某些有益而重要的東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能夠汲取哪些,轉化的途徑又是什麼?——當前,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中國最有價值的當代藝術必定是從中國文化根基上生長出來的藝術,而水墨又是其中最重要的類別之一。由此不難明白,邱振中所提出的這個問題對於整個中國水墨、整個中國當代藝術是何等重要。
當然,在這篇短文《出發點與線條的對比》中,書法仍然是談論的重心。“點”與“點”,然後形成“線”,這是書法和中國畫的核心。邱振中對馬蒂斯和版畫的重新演繹運用了水墨中點和線的筆觸。Michael Knight在他近期舊金山亞洲美術館展覽圖錄論文中,提及孫過庭(西元648-703)的話,“你必須瞭解點與線的運用,並大量地研究字元的歷史發展”。「1」
作為一位成就非凡的現代書法家,邱振中對中國書法中所積累的技藝深有會心。面對馬蒂斯畫作和中國版畫,邱在筆觸婉轉中閱讀、理解這些巨作,從細節到技藝再深入精髓。
馬蒂斯(公元1869−1954)是許多20世紀中國頂尖藝術家的重要創作靈感,特別是那些曾旅居巴黎的藝術家。馬蒂斯,野獸派運動的鼻祖,色彩大師,同時對線條深有研究。受到馬蒂斯影響的中國藝術家不勝枚舉,但是一般會想到常玉(公元1901−1966)和林風眠(公元1900−1991)。常玉作品中,尤其是他的裸體素描,油墨和木炭的紙上作品,是對比邱振中近期作品的最佳參照。常玉的作品,簡潔、優雅,筆下生花,神髓力顯。常玉對於線條的駕馭力無與倫比,得益于他早期多年的中國書法和繪畫學習。常玉旅居歐洲後,除了水墨,他也開始使用鉛筆、木炭、油彩。
邱振中將馬蒂斯作品中一些豐厚油彩的布面油畫作品詮釋成大型的紙上水墨作品(《馬蒂斯組畫》),也包括一些小型“習作” 。邱對馬蒂斯的研究包括重新演繹馬蒂斯1925年作品《Nu assis sur fond rouge》。其原畫是一位裸體女性坐在紅黃相間的條紋椅子上,強烈的紅色背景撲面而來。在邱的演繹中(未在本圖錄展示),線條被明顯簡化,色彩基調也轉灰色,女性裸體尤為突出,佔據了畫面的主導地位。女性的線條由宣紙上的灰色陰影所勾勒,較採用淺色的條紋椅,更為深邃。
在色彩的運用上,馬蒂斯指出藝術家“必須先從培養如何抓住神髓,再經過多年訓練、準備之後,年輕的藝術家才可以觸及色彩……”「2」也就是說,色彩不能成為干擾。這個觀點與傳統中國水墨相似,相對筆觸精良的線與點,色彩只是輔助。現代美術館(MoMA)策展人Ann Temkin在其錄音筆記《舞之一》中說到,“1908年,在馬蒂斯創作《Nu assis sur fond rouge》之前,馬蒂斯提到‘如果我要畫一個女人的身體,首先,我要捕捉到那種神韻;但是我知道我必須付出很多。我會將對身體的訴求縮小,去追求其基本線條。第一眼看去,魅力可能會減弱,但是真正的魅力會從最終創作的畫面之上油然而生,更具力量、深度的意義從而誕生,一個更為豐滿、完美的人物。”「3」邱振中的水墨作品初看與馬蒂斯原作截然不同,但仔細玩味,兩者在優雅、生動上保持著高度的一致。
邱振中對馬蒂斯的欣賞遠遠超逾他2003年在巴黎逗留兩個月期間,在龐畢度中心所看到的馬蒂斯作品。激發邱的靈感的作品不僅限於馬蒂斯的布面油畫,馬蒂斯的鋼筆淡彩畫及雕塑同樣也啓發了他。邱振中的另外一件小型水墨習作則來自於馬蒂斯的著作《舞》, 這件作品有兩個版本,《舞之一》(1909)和《舞之二》(1910),前一件是後一件的初版。在兩個原型版本中,馬蒂斯簡化了人體,將非本質性的部分省略,創作出力量充沛、象徵歡娛的化身,五位裸女環繞著舞蹈。邱在2012年所作的較小習作《馬蒂斯 ·旱金蓮花和舞蹈之一》裡(第x頁),只採用了原畫中最左邊的兩位。他用連續的行筆線條,將前方人物的手臂拉長。左側的舞者的軀幹和她伸展的手臂亦形成一個連續的、自信的連貫線條。與之形成对比的背景則由柔和的、散開的灰色抽象色塊圖案組成。
在對馬蒂斯的重新演繹中,邱振中還將點的運用大加發揮。在大型組畫作品中,濕墨散點將畫面中的織物和靜物烘托得更為生動。也就是在這樣的大型組畫作品裡,中國水墨畫的獨特品質呼之欲出。兩幅2012的作品《馬蒂斯第一組畫之一:工作室中的女人體》(第x頁)及《馬蒂斯第一組畫之二:鏡前跪着的女人體》(第x頁)都有真實的體現:與馬蒂斯的原作不同,無論是倚靠著抑或是跪著的裸女,邱呈現的連貫線條及圖案複雜而細緻。《馬蒂斯第一組畫之二:鏡前跪着的女人體》是根據馬蒂斯1937年的白紙上鋼筆素描作品《Nu devant le mirror》而作。邱的版本保留了原作描繪裸女的自信線條,而邱作中裡顯現的並排線條及多樣的裝飾圖案,給作品整體帶來了豐富的視覺效果。只有像邱振中一樣對中國水墨非常熟練的藝術家才能達致這種境界,成功的關鍵,就是在感覺的最深處,深深融入馬蒂斯的風格中,同時在那裡找到中國偉大傳統中與之契合的要素。
邱振中2012年年底創作的《馬蒂斯第三組畫之一:風景》、《馬蒂斯第三組畫之二:頭飾》、《馬蒂斯第三組畫之三:站立的裸女》是對法國現代藝術大師的繪畫及雕塑作品致敬。邱手握吸足了濃黑墨汁的畫筆,充滿活力地在紙上淋漓盡致地揮灑著,創作出極具張力的作品。
中國文學經典著作《西廂記》的明代版畫插圖,是邱振中在馬蒂斯之後精心的選擇。馬蒂斯—邱振中—西廂記,在這三重交織的關係中,《西廂記》的加入使三者之間的張力達到一個臨界點:西方現代—中國當代,中國當代—中國傳統,中國傳統—西方現代。邱振中把自己推到了這些對立面的中央。
印刷是中華文明最輝煌的成就之一,歷經了延續千年歷史的發展。邱振中將印刷中的線條化為筆觸中的線條,這樣的創作已經遠遠超出解構行為,而應視作更大的進步。邱的作品完全依靠筆觸到達之處的細緻、精準去創造人物形象和所處環境。早在公元8世紀,印刷品在中國即是大量生產,將紙張壓入雕刻有圖案和文字的木刻版上。單色的印刷即是如此完成,接下來再進行多色的印刷加工。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印刷品就是在中國被發現,公元868年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個横向展開的卷轴,現存於英国倫敦的大英博物館。「4」展開這個卷轴,首先是圖畫,釋迦牟尼和他的弟子須菩提,以及其他的早期追隨者。接下來繼續展開的部分則是佛教經文。此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由探險家斯坦因(Aurel Stein)發現於中國西北部的敦煌石窟。
邱振中用《西廂記》中的插圖作為出發點,以明朝弘治年間(公元1487−1505年)的版本所敘述的廣泛流傳、家喻戶曉的民間愛情故事作為靈感來源。1498年的版本是最早、最完整的印刷版本。如《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樣,此版本是插圖和文字相結合。《西廂記》中,插圖在頁面的頂端與圖畫下方描述的故事情節相互呼應。從明朝開始(公元1368−1644年),白話文學即採用木版印刷。1498年的版本中,《西廂記》由當時的畫家進行插畫創作,在1639年的版本中,著名畫家陳洪綬(公元1599−1651年)亦參與了創作。
元朝的劇作家王实甫(公元1260−1336年)改編雜劇《西廂記》取材唐朝詩人的浪漫傳奇《会真记》(又名《莺莺传》)。在王实甫筆下,故事角色惟妙惟肖:張生、崔夫人、崔莺莺(崔夫人女兒,與張生相墜愛河)、以及令人難忘的婢女紅娘(助莺莺和張生暗通書信而成功幽會),這些人物為当代水墨的詮釋提供了充分的素材。張生和崔莺莺私秘幽會,終成正果,情緒高漲,當然也極富喜劇元素,同時叛軍和其他負面人物一一登場,危機時刻穿插始終。
《西廂記》的熱門場景已經無數次地在陶瓷和雕刻,以及各种中国艺术及材料中被詮釋。邱振中以中國水墨創作重新演繹,正如馬蒂斯系列作品一樣,作品分為第一系列、第二系列、第三系列和習作。《西廂記第一組畫之一:鶯鶯與紅娘》(第x頁)和《西廂記第一組畫之二:思春》(第x頁)是邱創作于2008年的兩件大型繪畫作品,其中鶯鶯和婢女紅娘的親密關係可以從她們的肢體語言中观察到。紅娘通常是關切著鶯鶯,雖然邱採取了人物的不同大小以区分她们的角色,但她們的姿態和手勢更為精確地表示了她们的角色。畫作的背景是鶯鶯的閨閣裝飾或庭院佈置,採用相比人物更淺的水墨筆觸,畫作中的人物或人物關係非常突出。第一組畫成功地以水墨來轉寫木刻線條,除開水墨淋漓的繪畫感覺不談,它們把帶有大眾文化性質的木刻畫轉化為優雅的文人畫風格的作品。這種轉化在中國當代藝術中具有重要意義。當代藝術大量地把傳統世俗化、大眾化,從來見不到把世俗化、大眾化的因素逆轉為另一類藝術的例子。
《西廂記》第三組畫中的人物關係以更狂野的方式演繹。純黑色調中的墨色,顯現出線條的速度與流動感,略去了頭部的人物形象和空白的背景間對比強烈。這些充滿力量與生命力的繪畫,無論是在形式或表達方式上,完全是當代的演繹。畫面中飄動的衣襟,在如此厚重筆觸的描繪下極具視覺感染力。木刻版畫依賴文字和精細的背景圖像傳達故事情節,邱的作品卻僅僅專注於他最感興趣的部份。
創作木刻版畫的第一步是製作原稿。然後將上水的原稿反轉過來攤在平整的木板上、固定好。隨後,工匠在木板上雕刻繪上的、畫上的或寫上的原稿。之后再将木板刷上墨,在印刷機中加壓形成原稿的複製品以完成印刷。精確雕刻的圖像和文字清脆、銳利。邱振中的《西廂記》創作中,則利用許多與原版相比分散、模糊、柔和的線條,使場景在整體上更顯浪漫。原本的木版插畫與邱的創作絕不可能相互混淆,邱的大型組畫亦不會被誤認為原始木版畫。
邱振中深諳“臨摹”。作為一位高度訓練的書法家,他習得了實用的水墨技藝,用以臨摹過往大師的傑作。正如邱在其展覽介紹中所述,他對馬蒂斯和《西廂記》木刻版畫的重新創作動機正是源於臨摹之法。在中國,臨摹是公認的教學之法,被廣泛認可和鼓勵。漢語語境中的“臨摹”則是“複製”之意。但是,相比英語語境的“複製”之意,漢語的“臨摹”包含更多細緻入微的意義。
邱振中開創先河,認為他的作品是概念化的創作。傳統的臨摹之法基本上是去效仿原作和被臨摹的模式,採用同樣的材料(毛筆、水墨、顏色、紙張)以及和原作同樣的技藝。然而,邱從啓發他創作的原作出發,最後脫離了原作,尤其是他對馬蒂斯的臨摹。在邱的創作中,馬蒂斯的布面油畫和《西廂記》木刻版畫都變成了自由灑脫的紙上水墨。中國傳統中,對原作非凡的臨摹作品其自身亦被視為傑作。藝術家的精神過程包括了對原作的理解、吸收和模仿。擁有相應的高超技藝是前提條件,然而提高創造力則是這一過程中至關重要和最為基本的過程。“模仿”大師作品風格(仿)和“複製”大師作品(臨摹)被視為相當高尚的創作練習。邱振中對於線條的決心和線條運用的迷戀,使得他對馬蒂斯作品和《西廂記》木刻版畫的詮釋成為其追尋當代艺术轉型的堅實出發點。選擇前人的偉大作品,甚至忠實地保留原作的某些成分——例如構圖,都成為邱振中的策略:那些保留的部分,正強烈地襯托出改變的部分是何等的重大、激烈。這些改變之處,正是邱振中所關注的中國當代水墨問題的核心。
毛岱康
2012年10月
毛岱康是一位擁有廣泛學術興趣和多重事業的獨立學者。她是亞洲藝術和文化領域的資深顧問、教育家、作家和發言人。毛岱康出生和成長於多倫多,早在學習漢語、美術、歷史和文化還未成為時尚趨勢前,她就已經全部涉獵。 1981年,毛岱康以本科和碩士雙重學位的身份畢業於多倫多大學,同時她也是康諾特研究學者;隨後她移居北京,以加中學者的身份在中央美術學院訪問和研究。其間,她在中央美術學院研習藝術史,頻繁參觀故宮博物院的收藏,並遊歷中國大江南北,拜訪佛教和重點文化遺址。其後,毛岱康作為聯邦學者重新定居香港,並密切關注中國和整個亞洲藝術的發展。
腳註:
「1」Hans Herman Frankel,引進、翻譯和評論,關於中國書法的兩篇專題著作(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1995),14頁;Michael Knight 引述《簡介:解讀中國書法》,《字符以外──中國書法解碼》(舊金山:亞洲美術館,2012),21頁。
「2」“馬蒂斯給Henry Clifford的信,威尼斯,意大利,1948年2月14日”,Herschel B. Chipp,現代藝術理論(伯克利和洛杉磯:加州大學出版社,1968),140−141頁;引述自Rita Wong論文《常玉——短篇傳紀》,網上來源:http://www.asianart.com/exhibitions/sanyu/wong.html
「3」錄音日記文本版來源於 http://www.moma.org/collection/browse_results.php?criteria=O%3AAD%3AE%3A3832&page_number=46&template_id=1&sort_order=1 ,現代美術館(MoMa)中的馬蒂斯收藏還有相當數量的藝術家肖像畫,展現藝術家對於線條的駕馭。
「4」關於文字歷史、創作和保護的描述,參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世上現存最早的印刷書的故事》(倫敦:大英圖書館,2010),Frances Wood,大英圖書館中國部負責人,以及Mark Barnard,大英圖書館保護部經理,負責了此圖書7年的保護和珍藏。
「5」中文版的文字可以在Gutenberg網上瀏覽:http://www.gutenberg.org/ebooks/23906,英文版本由Stephen H. West 及 Wilt L. Idema 翻譯、編輯並附上簡介,《The Moon and the Zither-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1991)。